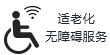郑以禄和他的寿州香草传承
一、
去年的年里年外,东园白菜卖到了四块钱一斤。
腊月的时候,我在“三步两桥”附近遇到郑家庄的郑以禄老人,要他帮我弄两蛇皮袋的“黄芯乌”白菜送人,他把一颗花白的头颅摇得跟拔朗鼓似的,对我说:“政府贴出告示,东北拐塘清淤,造湿地公园。菜地征收,钱已打到各家的账号,一律不准再种菜,以免影响施工”。我一听急了,忙问香草地怎么办?老郑说:“我们打了报告,政府重视香草传承,特将报恩寺后面的那片香草地保留下来了”。
二、
中国上古时代认为万物有灵,花草树木,山川雷电等等,被赋予灵魂之后,既可感应上天,获得生命力量,又能佩饰自身,消灾避祸,护佑众生。提起香草,我们会想到2000多年前楚国的士大夫,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,在千古传诵的《离骚》中,他用“香草美人”构筑了一个庞大而又隐秘的比喻系统,表达他高洁的精神品质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。南楚之地,草木有灵。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《离骚》中有种类繁多的香草,江蓠、蕙、杜若、荃、茹、留夷、薛荔、芰荷、白芷、秋兰、菊等等,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。这里所说的“江蓠”,即是寿州香草。
关于寿州香草的溯源之考,目前我们看到的乡帮文献中,嘉靖《寿州志》不载,光绪《寿州志》只把它列为“食货志”草类的最后一位。清朝雍正年间,从寿州析出凤台县,同城划境而治,嘉庆十三年(1808),来了一位“大清名宦”李兆洛先生做凤台知县后又兼理寿州,他在《凤台县志》“食货志”里经过考证,指出:“江蓠,土人谓之离乡草,惟报恩寺后产之。或种以为业,十月布子,四月而刈,镬汤煮之,纳诸坎,蹈以出汁,经宿而暴之,气类苏荏,妇女以渍油膏发,远方多来售之者,其草出境乃香,故谓之离乡草云。”在这段文字中,李兆洛先生从香草产地、种植、收割、加工、售卖以及“离乡草”之名的得来,更有深加工开发产品“渍油膏发”等等,可以说后世有关寿州香草的一切之说,皆滥觞于此。
三、
关于寿州香草的由来源自传说,其一是乡愁忠魂说:这是一则凄凉的故国挽歌。楚国从长江汉水再到淮河岸边,在郢都寿春过完了最后的十八年。公元前223年,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倾国而来,楚将项燕率60万大军迎战,双方在平舆暴发了先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。楚败。秦军夺取淮河两岸的大部分地区,攻拨寿春,杀楚将项燕,俘楚王负刍,楚国灭亡。寿春都城,万千宫殿,化为乌有,唯有一枝香草在风中不屈不折地摇曳。楚国将士,流血牺牲,忠魂所凝,化为香草。亡国的背井离乡的楚人,不会忘记长眠故土的将士。他们携带的故国的香草去流浪,离开家乡愈远,其香益浓也,愈能勾起他们的乡愁,而且每逢阴雨,其味越香,因为离乡后的思乡之故,“离香(乡)草”因此得名。
其二是战马助驾说:“赵匡胤困南唐”的故事在寿州大地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在本地流传甚广的“芋头的故事”、“大救驾故事”等皆衍生于此。现在,又将一枝小小的寿州香草与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扯上了关系。相传在五代十国末期,后周大将赵匡胤率军攻打南唐寿州,夺城之后,他的战马挣脱缰绳,径直跑到东禅寺边上的一块草地吃草,打不跑,牵不走。赵匡胤闻知后,便来实地察看,摘了一枝野草嗅嗅,连声说道:“是香草,是香草”。吃了香草的战马,犹如神助,铁蹄征伐,所向披靡。寿州香草以此得名。
其三是佛法开示说:传说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贞观年间,玄奘法师受皇帝敕令来到寿州报恩寺传授佛法。一天晚上,忽然闻到寺庙外有一阵阵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,玄奘自知佛法已显,立即和住持僧面北跪拜。次日清晨来到寺庙后院一看,青草一片,白花朵朵,幽幽奇香,散发开来。这个传说有着浓郁宗教意味,一方面说明寿州香草气是受了佛法的开示和香火的熏陶。另一方面,道出寿州香草有一种认土归宗的执拗劲,也进一步表明它的稀缺和珍贵。无论哪个朝代,也无论疆域多么广大,它只认城内报恩寺周边的一小块地儿。
但现实中的寿州香草是怎样的呢? 2016年,古老的“寿州香草”获权威定名。当年有报道称:“寿州香草为濒危物种,是两年生草本植物,茎圆中空,高一米左右,叶对生,花柄长,形似芝麻秸,每年九月下种,次年四月收割。目前仅在寿县古城报恩寺东菜园有数亩种植。
为了保护安徽寿县芍陂(安丰塘)及灌区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,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曾在堰口镇开展寿州香草保护性繁殖,同时申报了中央财政农业技术推广项目。后来又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俞年军、安徽省种子协会主席许正嘉等植物学专家,实地考察寿州香草东菜园种植区、堰口镇保护性繁殖区,并香草植株标本带回安徽中医药科学院详加考证。得出权威鉴定,寿州香草被定名为白花草木樨,系植物界、被子植物门、双子叶植物纲、蔷薇目、蝶形花科、草木樨属,白花草木樨种(Melilotusalbus Desr),否定了以前网络流传的堇菜目、报春花科、珍珠菜属的说法。
四、
在郑家庄,郑以禄老人领我来到巷道深处的一口老井旁,他告诉我,此井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,是郑氏家族迁居寿州城内报恩寺附近的见证。郑氏家族于清代咸丰九年由凤台县顾桥迁徙而来,家人未到之前,先打一口井来“定定根”,谓之“家井”,从此围绕井栏,聚族而居,代有人才,逐步兴旺发达起来。到清代光绪年间,祖、父辈虽然没有博得大的功名,也出了数名秀才,或从政、或经商、或从医、或农耕,其中先祖父郑辉斋先生秀才出身,在东菜园旁的火神庙设馆办学,培养众多弟子,声名远播。到解放前,历经九代,有200多年,郑氏家族始终没有离开过东菜园这个大本营,郑家庄由此而得名。
郑禄老先生出身于1948年,1965年初中毕业后即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,从那时起,他就开始在东菜园从事香草耕种。幼年的耳濡目染,先辈的传授,成年后田间地头的操劳,几十年来的坚守和探索,使他对寿州香草的习性了解,从耕种到收割,犹其是土地的翻耕、种子的保管、成熟期的收割及一系列复杂加工技艺过程,直到做出香荷包等产品,都了如指掌,成熟在胸。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大队集体劳动,每到香草收割之时,郑以禄就派上了用场。他必须时时观察天象,又要天天察看草色,判断成熟程度,以便在香草成熟恰当,天气晴好之时,决定收割。香草的收、烫、窖、晒,必须一气呵成,不能间断。郑心禄带头指挥,大家从头天下午要一直忙到第二天“五更头”天快亮。最难的还是香草的售卖,那时没有运输工具,全靠徒步拉车。两人一组,带上咸菜馒头,郑心禄每年都到霍山、肥西、湖北英山等地销售香草。“文革”期间,有一阵子把香草视为“资产阶级毒草”,不准耕种。这可急坏了老郑。他心里清楚,香草是两年生植物,必须是当年留好种子。如果隔年,或不发苗、或植株变异、或没有香味。这样的活,寿州香草将面临绝种的危险。老郑想,香草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,不能在我们的手上断绝。那几年,他悄悄垒高围墙,又喂条凶狗,偷偷在自家院中种植。不是为卖钱,而是为了保存香草的种子。
1981年包产到户,老郑家分得报恩寺后面的几亩土地,他如鱼得水,抛开膀子种香草。凭着从小就了然于胸的种植经验和秘不授人的种植决窍,老郑使出了种植香草的“绝招”,他种出的香草声名日隆,每到端午时节,往往供不应求。但那些年也仅仅是卖草为主,小打小闹,不做产品,收入不高,仅是补贴家用。
寿州城内的东北隅,是一块神奇的风水宝地。在这个狭小的区域内,聚集了众多的寺庙庵观,如报恩寺、东岳庙、准提庵、八腊庙、三圣庵、火神庙等等,是古时候人们重要的祭祀的地方,有的庙宇不在了,沦为住宅或菜地,它的地气还保留着。但寿州城内属盐硝地,过去产硝,土质板结,加之城东北地势低洼,整个东半城的雨水从马营塘、洒金塘、傅家塘经“三步两桥”汇集到东北拐角塘,再经“崇墉障流”涵洞流到城外。每次涨水,最先受涝的是东菜园。但是,就是这样的土地,却种出了神奇的寿州香草。老郑说,讲寿州城内是“筛子地”,水会自动渗下,不会水淹。那是鬼话。听老人们说,解放初时,每涨大水,如临大敌。县委书记赵子厚曾拎着盒子枪在城墙上巡逻。有一年水不,涵洞渗漏,是我冒死下去堵的木头塞子。后来公社规定,东北涵洞“崇墉障流”归东园村管,西北涵洞“金汤巩固”归西园村管,都派有专人负责。
大集体的时候,爱折腾,瞎指挥,东园曾经种过白芋、大麻和薄荷等,但收成不好,品质不高。“赵匡胤困南塘” 的传说故事里,就有遇见“芋(遇)头”一说,但东园种出来的芋头,奇大奇丑,疙里疙瘩,外皮开裂,肉质粗糙,吃下去味同木屑,最后拿去只好喂猪。几经折腾,后来终于又回到种菜上,但种出来的“黄芯乌”白菜就不一样了,梗短叶肥,少筋多肉,赛比羊肉。种香草是祖传之技,非“报恩寺周边土地”莫属,郑以禄老人凭着几十年来对东园土壤、水质、气候、日照、施肥、耕种时节、收割时期(其中秋季播种、冬季看护、春季观察、夏季收割),收割后通过水烫、窖焖、晾晒,直到做出产品的深刻了解,尤其郑氏先祖在清朝光绪年,建于报恩寺东侧的香草草窖,为了复原,他遍访先人,又凭着小时候的记忆,重新建造了香草窖池,窖闷是香草制作中的一道至关重要的工艺,有着不可告人的诀窍。凭此,郑以禄一跃成为寿州香草种植能手。
郑老还在发明了一种套种方法,香草秋季下籽后,冬季寒冷,香草种籽蛰伏在土地里没有发芽,套种白菜,白菜顶雪,抗寒防冻,等到春暧,铲白菜连带松土,香草即冒出芽了。至于白菜与香草在东园相遇,有没有其他秘密物语,吾辈就不敢妄猜了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,香草绝不可以异地种植,如果离开,则枝叶照发,空茎变为实心,香气尽失,谓之离乡草者,远离故土,其香益浓也,而且每逢阴雨,其味越香,传说是因为离乡后的思乡之故,这是“离香(乡)草”得名的真正原因。
郑老时常跟我开玩笑说,我可不是一个单纯会种香草的农民,我小时上过私塾,初中毕业,成绩尚好,主要家里是小土地出租者成份,升学无望,又不给当兵,种香草既是热爱,也是命中注定。小时候听大人讲,寿州状元孙家鼐回乡省亲,曾将香草带到京师,敬献给他的学生光绪皇帝。民国时期的淮上名士,革命先驱柏文蔚先生,在见到他敬仰的导师孙中山先生时,送的就是寿州香草作为礼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,一个老先生突然找上门来。原来是郑家过去的雇工周小山从台湾回来了。周家清贫,帮郑家种地为生,主要是种蔬菜和香草。那次到淮南田家庵去卖香草,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后来到了台湾。他回来找“老东家”,除了给父母上坟,主要念想的还是自己曾经种植过的香草,那一缕浓郁的陈香拂过,将漂泊的游子揽入故土的怀抱,令他在香草地嚎啕大哭,从此至死,须臾不离。
五、
2017年,寿县被文化部公布为全国35个端午习俗集中分布区,安徽省仅此一处。中国之大,习俗之广,寿州为何能登榜胜出?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。它源自上古初民的天象崇拜和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它兼收并蓄,将多种民俗融为一体,逐渐形成了赛龙舟、吃粽子两大礼俗主题,并和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寿县作为楚国之都,文化底蕴深厚,自有独特的端午节民俗。与江淮大多数地区一样,寿县端午节主要有包粽子、吃咸蛋、炸“鬼腿”、挂艾草、赛龙舟、饮酒吟诗等习俗,还有一个重要习俗,就是佩戴用当地种植的香草制作的香囊。端午节小孩佩香囊,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,实际是用于怯臭、驱虫、避汗气和点缀装饰。香囊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,形形色色,玲珑可爱,清香四溢。《寿县志》在风俗类记曰:“端阳节,孩童胸前佩戴当地特产香草碾成细末佩以其他香料缝制的香荷包,以作驱疫免灾之用,此俗至今尚行”。端午节佩戴香囊成为最具楚文化仪式性的特征的习俗,孟堃先生编著的《古寿春漫话》里说:“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,在寿县别有一番情趣,就是人们佩带香荷包的风俗。至今不衰。香荷包主要原料是香草。香荷包的制作方法,是把香草剪成米粒大小的碎末,再放入同样大小的碎艾草、艾茎,喷以少量白酒,捂盖片刻,香气四溢,装入彩色小布头缝成的小袋即成。香荷包有各种形状,因人而异。老奶奶、老爹爹(寿县方言:约为北方的爷爷)们多佩团形,布色宜素;新媳妇、大姑娘们,多佩红色、绿色、彩色;小毛丫、小毛孩,佩带的式样和色彩均大大超过前者,有做成瓜形、葫芦形、椒子形、石榴形、桃子形、小猫、小狗、娃娃形的。还有用‘男红’、‘女绿’分之”。
2017年11月,郑以禄老人成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项目—寿州香草传统制作技传承人。他总结了离香草的作用:
进门香--挂在门上,作招福、辟邪、镇宅之用。
凝神香--置于枕边,有安神、助眠、除瘴之效。
护身香--戴在胸前,防病害、驱百害、祈鸿福。
平安香--悬于车内,可凝神醒脑,保一路平安。
养心香--放在屋内,灭菌驱虫,净化美化居室。
六、
正是春草葳蕤,春花烂漫的时节,漫步城垣,远望则淝水汤汤,八公苍苍。近视则菜园青青,城塘澹澹。今年东菜园遇到历史从没过的大变局。大型挖掘机掀起了城河的淤泥,园里弄了个底朝天。不久的将来,昔日的菜园变身居民休闲的湿地公园。但是,香草不会消失,规划中这里还将会出现一个古色古香的“寿州香草文化园”。时值农历三月十五日。报恩寺里,梵音阵阵,一年一度的水陆法才刚刚开始。而更远的苍茫的八公山上,三月十五古庙会的万千香客,正沿着屈折的盘山之路,潮水般的涌向山顶辉煌的帝母宫。
郑以禄老人不为所动,他坐在香草地的小马轧上。春天万物萌生,杂草尤盛,他在给香草除草。去年秋冬寒冷,阴雨过甚,加上清沟沥水不及时,香草种籽发芽不多,今年只够留种。我们正说着话,忽然从田埂的那头飘然而至一位美少年,是郑老先生的孙子,这位刚刚接到中国舞蹈学院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文艺高材生,目前也是寿州香草文化创意产品的主要设计者之一。郑氏家族的香草传承有了这位时尚新潮的新生力量,在与古老的碰撞中,又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?此刻,少年正在手机里玩着《仙剑奇侠传》的大型游戏,其中人情跌荡,生死别离,令人唏嘘。戏中有这么一出:女儿梦璃在离家行走天下前,养父突然赠送来自古寿州的“离乡草”香香囊一枚,让她无论走到哪里,身边都有家的味道。结果女儿为了家族的命运留在瞑界,天人永隔之际,她又把草香香囊托人带回给守在故土的父母,以表达今生不能赡养之恩和永世的思乡之情。这正是:
一株草
只记住扎根的一小块土地
一株草
慢慢进入种植人家族姓氏
一株草
香气拂过口鼻进入我们的身体
一株草
有了很强的归属感和方向感
端午节的时候
从长江到汉水,再到淮河……
乘风破浪,往回赶
避开瘟疫、虫豸、蚊蝇
赶回在楚国基因里已经注册的故乡
 皖公网安备 34042202000005号
皖公网安备 34042202000005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