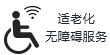【寿县年味】春节与“童言无忌”
文/汪守兵
儿时的父亲是无神论者,过年过节不像母亲那样循规蹈矩,讲究迷信。但有一条父亲特别较真----就是忌讳说不吉利的话。
大年三十,年味达到了极致。父亲贴完春联,坐在灶前帮母亲烧火,厨房烟雾缭绕,香气弥漫。母亲正忙着煮菜,蒸花馍馍,她揭开锅盖,随口说道:“坏了,坏了,水烧干了!”
父亲起身探望,立刻面露愠色,怒声道:“说什么呢,一惊一乍的!”
此时,“坏”、“穷”、“破”、“完”、“死”等都被父亲列为禁忌之词。母亲意识到自己采中了“雷”,也不敢作声,只顾低头忙碌……
巴金《家》中有段文字:“老太爷因为觉群在堂屋里说了不吉利的话,便写了‘童言无忌,大吉大利’的红纸条,拿出来贴在门柱上。”
父亲和巴金笔下的老太爷有几分相像。那个年代,写春联是过年的一部分,而村里村外会写春联的人极少。父亲读过私塾,练就一手很好的毛笔字。叔叔、大爷们早就把红彤彤的门对纸送到我家,请父亲帮忙书写春联。父亲从不拒绝,一写就是好几天。不管给谁家写,“童言无忌”是必不可少的一副。
“童言无忌”的原意是:小孩子天真无邪,说话直来直去,没有顾忌。旧时过年,大户人家的厅堂里多贴此四字,意思是孩子说了口无遮拦的话,若冒犯了神灵或者来客,敬请他们宽宏大量,不要介意。
我家虽算不上大户人家,但也算是书香门第。春节贴“童言无忌”的习俗也不知传承了多少代。它甚至成为我们心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词语,被广泛使用。譬如,有谁说了不合适的话,或不吉利或伤及他人,另一个人就会用“童言无忌”加以补救,化解尴尬。此时的“童”字自然已突破了年龄的限制。
待我出身工作后,写春联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,父亲则在一旁替我打下手,提供春联的内容。诸如:积善堂中无限乐,长春花下有余香;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。还有,抬头见喜、六畜兴旺、出入平安、童言无忌等等。
每逢佳节倍思亲,父母先后离开了人世。过年的许多习俗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写春联变成了买春联,客厅里再也难见“童言无忌”之类地春联了。但它早已深藏于我们一代人的心里,并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话语之中。
这不,除夕的上午,我和老婆贴好自家的春联后,急急忙忙地趋车赶往岳母家团聚。路上堵车比往年更严重,有人强行加塞,险些撞上我的爱车,愤怒之下,我不禁暴了粗口。老婆一句“童言无忌”立即唤醒了我对过年和父亲的敬畏之情,怒火随之烟消云散。
不知道“童言无忌”算不算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?


汪守兵,笔名老墩坎,安徽省寿县作协会员,中学教师。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散见于《文学百花苑》《荒原诗刊》《诗中国杂志》《中国乡村杂志》等纸媒和多家微平台。并有作品收录于《新时代诗词集萃》《中国荒原诗人诗选》《中国最美爱情诗选》《中华诗人作品年选大典》《大爱真情》等。
编辑:申思雨
初审:赵允洁
终审:蒋 兴
核发:黄丹丹
 皖公网安备 34042202000005号
皖公网安备 34042202000005号